
品读新疆
制作一块寻常牧民家的毡子
要经过剪晒羊毛、打散羊毛、洒水粘连
席卷捆紧和手擀压实等步骤
![]()
点击音频收听《雨洒羊毛一片毡》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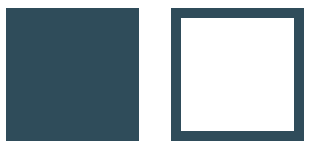
自从上次在山里,和朋友搭完毡房后,我就开始对羊毛毡念念不忘。每次下乡进山,在农牧民家里,总会看见或铺或挂在房里的羊毛毡。有些毡子虽已泛黄,却散发着温暖气息。
我喜欢看这些毡子,看中轴线两侧布局对称的花纹,看用简单线条勾勒出的丰富图案,看明亮绚丽的色彩,看它们表面隐隐探出头的细羊毛,以及阳光照进屋内、坐在毡子上淳朴的人们。
幸运的是,几天前,我在古丽家亲自体验了擀毡、制毡的过程,很美妙。

我们把晒好的羊毛,摊放到庭院里的凉床上,先取一小部分平铺到地上,当然下面会垫一大块布料。听到要制毡,邻居们纷纷来帮忙,小孩也来凑热闹。几个人围坐在一起,开始将羊毛打散,因为这些羊毛大部分是黏在一起且呈团状的。比较有趣的是,敲打羊毛的木棍,多是红柳细棍,大家像约定好似的,用同一种节奏敲打。侧耳听时,柳棍划过空中时簌簌有声,如利剑出鞘般清脆;落地又如鼓点般绵密,节奏此起彼伏;再加上谈笑声,孩童嬉戏声,牛羊叫声,还有鸟鸣声,如交响乐一样丰富,也让这繁琐的劳动变得有趣起来。至于羊毛要敲打到多蓬松,凭着多年经验,他们都好像心里有数。
话说间,古丽站起身,朝院子里的厨房走去。再出来时,手里提了一个水壶,里面是刚烧开的水,壶口白色水蒸气在突突升腾。她径直走到里屋,又夹了一把扫帚出来。扫帚柄是用长竹枝扎的,扫帚头是用高粱穗、金丝草等人工编织的,看起来很干净,想必不是用来扫地的。只见她在扫帚上一边倒开水,一边上下翻转,直到水珠挂满高粱穗的每个空隙。接着,她用湿润的扫帚轻轻拍打已被敲蓬松的羊毛。羊毛迅速粘连在一起,原来开水可以迅速溶解羊毛角质,使其粘得更紧密、牢固。这让我想起明太祖朱元璋游猎时给儿孙出对子的民间传说,他出上联“风吹马尾千条线”,其一子对“雨洒羊毛一片毡”。可见古时人们便知羊毛遇水成毡,可见制毡工艺多么悠久。

制作一块寻常牧民家的毡子,要经过剪晒羊毛、打散羊毛、洒水粘连、席卷捆紧和手擀压实等步骤。古丽告诉我,后面几步尤为关键,也是最费体力的。
所谓擀毡,就是将打好的羊毛,用芨芨草垫卷起来,然后用几条结实点的粗绳子绕着捆紧卷成圆筒形,有些像用细竹帘卷紫菜包饭一样。我们几人并排跪着,开始用胳膊擀毡筒。其间,还要反复解开芨芨草垫,把成型的毡子铺开,再给上面洒些热水,再卷,重复多次直至毡子定型。我注意到,古丽还要在卷起的毡子两头不时洒些热水。心中不免感慨,这真是一门手艺活,处处都有学问。
我跪在中间,擀了一阵子,酸胀感即刻袭来,先是左右手肘处,接着是手臂、肩膀和颈椎,再是膝盖。尤其当我站起身来活动筋骨时,咔嚓几声脆响从关节处传来,酸胀感愈加清晰。脸颊、腋下和后背汗流不止。古丽笑着问我要不要喝点奶茶、吃点撒子,我摇摇头,她便低头继续擀制起毡子。
古丽一边干活,一边说:“现在日子好了,养的羊也多了。男人把羊照顾得好好的,女人就给羊洗洗澡、剪羊毛、做毡子。”神情里满是安逸和泰然。这一刻,我仿佛看见一种简简单单的幸福清风般飘荡在山谷间、牧草上、羊圈里和这庭院中,是属于他们独有的轻松与快乐。古丽还告诉我,现在挣钱的渠道也多了,不单单是卖牛羊,纯手工的羊毛制品也越来越受欢迎,所以每年都会做些羊毛毡来卖。

太阳开始西下,秋叶沙沙作响。两只小羊羔在我们身边,一前一后地走着、嗅着,好奇地看着。太阳的余晖洒在地上,到处都光影柔和。再看古丽,从脸颊到手背,还有她手中的毡子,都被金色光芒笼罩着,一副岁月静好的样子。
对生活在巩乃斯河的牧民来说,羊和羊毛毡与他们的生活须臾不可分离。每年开春,圈了一冬天的羊群,终于迎来早春转场;到了夏天,布满山坡的羊群,在风里自由地咀嚼青草;秋收前后,羊群排起长队跳进水渠,洗去一身尘垢;入冬前,人们做好羊毛毡,铺到暖和的家里。羊毛擀成毡,成为孩童手里的玩具,男人脚下的靴子,妇女手中的饰品,老人身上的暖衣……这些最本真、最简单的生活,成为一代代人心里的印记。
几天后,恰巧赶上古丽亲戚家的女儿举办婚礼。人们把花毡铺到干净的地上,院子里摆上烤肉架,再支起一口做抓饭的大锅,馕坑里的皮芽子馕香气扑鼻。抓饭、烤肉、馕热气腾腾端来了,还有树莓果酱、酸奶疙瘩、包尔萨克、巴哈利摆在花毡中央,参加婚礼的亲朋好友们席地而坐分享着食物,向一对新人连声祝福,欢声笑语不绝于耳。吃饱喝足后,有人弹起冬不拉,有人跳起黑走马,在秋日暖阳的暖阳下,花毡的色彩和图案格外明艳。
羊毛毡伴随牧民一生,也目睹他们的一生。(文/张振 图/我从新疆来微信公众号)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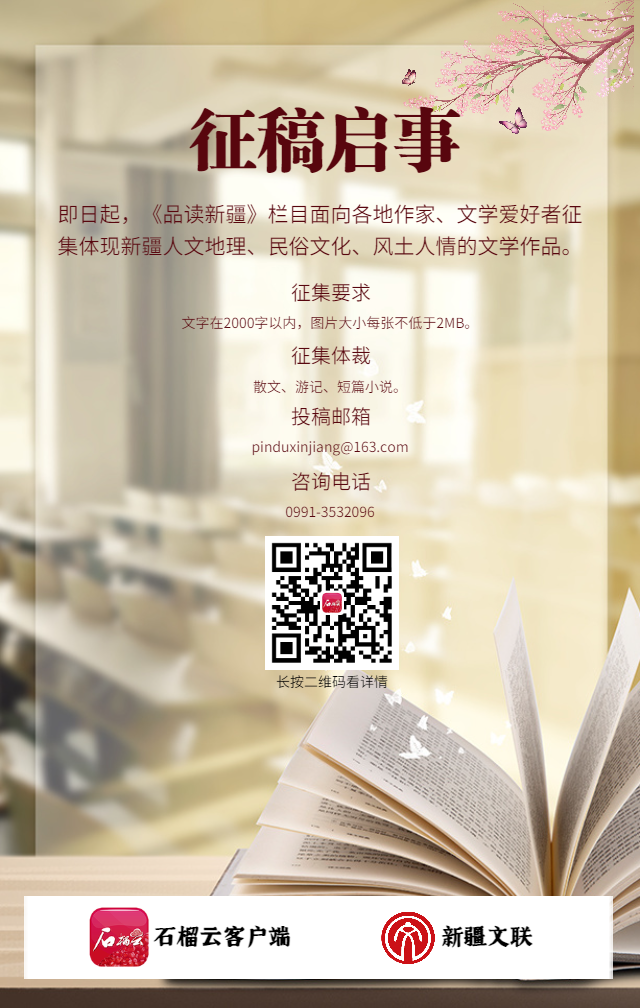
(版权作品,未经授权严禁转载。转载须注明来源、原标题、著作者名,不得变更核心内容。)




















最新评论: