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品读新疆
每天清晨天还未亮
麻雀便叽叽啾啾鸣叫起来
无论春夏秋冬
我都在它们的鸣叫声中醒来
时间长了
有一天听不到它们的叫声
便会觉得生活中缺少了点什么
心里感到不安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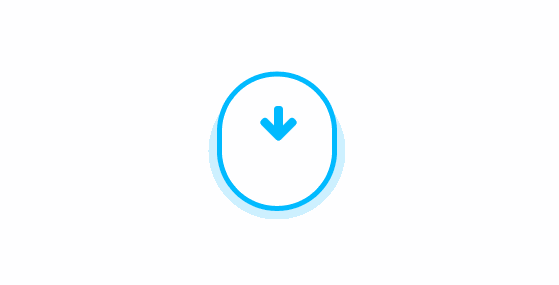
点击音频收听《麻雀为邻》
以前居住在团场连队时,我家四周都是高大的白杨树,白杨树上住着成群的麻雀,它们成了我家的邻居。
每天清晨天还未亮,麻雀便叽叽啾啾鸣叫起来,无论春夏秋冬,我都在它们的鸣叫声中醒来。它们叫醒我的时间随季节而变化,早晚也略有不同。时间长了,有一天听不到它们的叫声,便会觉得生活中缺少了点什么,心里感到不安。搬到军垦新城阿拉尔市居住后,很少见到树上栖息的麻雀,也听不到它们的鸣叫声,这让我怀念起居住在连队的日子。

在团场连队常见麻雀,它们成群结队地在院落中飞翔、觅食、嬉戏。仔细观赏麻雀:一顶土灰色的“帽子”戴在头上,一身迷彩服般的羽毛,黄澄澄的小眼睛总是好奇地瞅着四方,胖嘟嘟的肚皮上盖着一层软软的灰白色绒毛。这样一只活泼可爱的麻雀,就像一个十分机灵的小顽童,惹人喜爱。它们在我家四周高大的白杨树上筑巢,每天早晨,我站在院子里听它们在树上叽叽喳喳“高谈阔论”,或看它们在树枝间蹦来蹦去锻炼身体。若发现“情况”,它们便忽地一下惊慌飞起,在天空中盘旋许久,确定没有危险后,才小心翼翼地回到白杨树上,然后又聚在一起叽叽喳喳,十分热闹。
其实,麻雀可以监测噪音,这是科学家发现的。每当中午,我家门前出现人流不息、车水马龙的繁忙景象时,麻雀便躲起来,好像对人类的热闹并不感兴趣,甚至还有些反感。而当夕阳西下,熙熙攘攘的人流声渐渐退去,周围安静下来时,麻雀们又三个一群、两个一伙地跳出来,拍拍翅膀,舒展舒展筋骨,开始继续它们的“高谈阔论”,给疲劳了一天的人们带来大自然的轻松气息。

上世纪五六十年代,人们对麻雀认识不足,将其列入“四害”之一,用尽各种方法对它们进行大肆捕杀,使它们几乎没有藏身之地。直到后来发现麻雀每年要吃掉许多害虫,才使它们得以“平反昭雪”,被列为国家“三有”保护动物(指国家保护的有益的或者有重要经济、科学研究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),禁止任意捕杀,这才让麻雀有了生存空间,能够自由繁衍后代,快乐地生活在大自然里。
麻雀为了生存,大多以害虫和草籽为食,在找不到食物时才会对庄稼下手。常见到成群结队的麻雀在成熟谷穗旁飞来飞去,无人时会偷吃粮食,那只是为了果腹而已,它们从来不会大肆祸害粮食。
麻雀跳跃行走,类似澳大利亚的袋鼠。无论在地上还是树上,麻雀都会抖动全身,快速跳跃,敏捷而准确。我仔细观察,麻雀一般不会飞行很远,而是近距离盘旋飞行,忽而向左,忽而向右,或是为了寻食,或是为了寻找同伴。在人眼看来,所有麻雀的外形几乎是一样的,几只麻雀落在同一个树枝上,很难分辨雌雄或是否属于同一家族。它们之间很少发生争斗,总是和睦相处。与麻雀混熟了,它们有时会飞到我家的餐桌上寻找食物,在吃食时,两只小眼睛总是观察着四周,时刻保持警惕。它们体型小,身处劣势,所以时常要警惕天敌的袭扰。想想这些与我们在同一屋檐下生活的“邻居”,一辈子都在谨小慎微中度过,该有多么不容易。

冬季里,食物稀少,它们在草垛旁、雪地里寻找食物。连队的麦场是麻雀常光顾的地方,麦场堆有大量的麦草和稻草,里面有没打干净的麦子和稻子,它们就钻进草堆里觅食。谁家房前有狗或鸡没吃完的食物,或是掉在地上的食物,它们也不嫌弃;鸡鸭的剩饭,人们餐桌上丢弃的食物残渣,它们见到后便呼朋唤友来“会餐”,彼此礼让,从不发生哄抢。
在我家旁边有一棵高大的杨树,树上栖息着一窝麻雀。它们在树顶处筑有一个窝,用树枝或其他毛发筑成,这窝麻雀是一对夫妻和四个子女。它们一家六口时常叽叽啾啾地鸣叫着,感觉其乐融融、温情脉脉,这样和睦的家庭令人羡慕。
漫长的冬季,是麻雀最难度过的日子,它们会飞到很远的地方去觅食,路上还要躲避天敌。成群结队的麻雀在空中飞翔时,它们队伍后面总会跟着几只鹰或鹞子,有的麻雀飞得慢或躲避不及,便成为鹰和鹞子的美餐。看着同伴被捕杀,它们无能为力,只能大声鸣叫,令人哀伤。
生活在阿拉尔,感觉这里的城市喧嚣不适合麻雀生活。虽然城里也有树木,可都是矮小的绿化树,不适合麻雀筑巢。它们只好远离城市,到偏远连队的树木上筑巢了。
每当我听见麻雀的叫声,就会心生快乐,仿佛老友重逢。
文/肖良波

主播:李怡然
河北传媒学院
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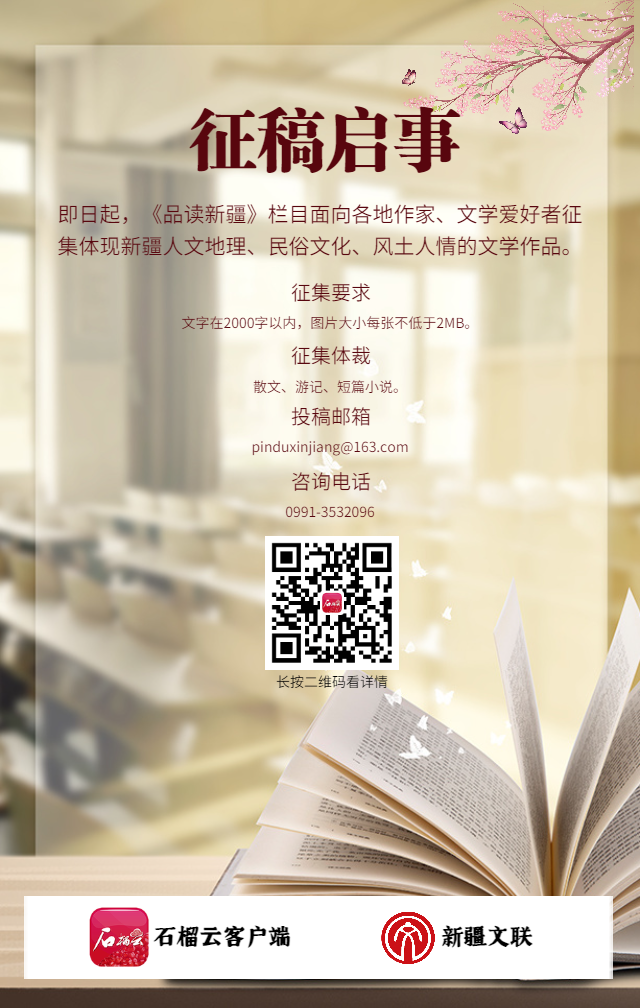
(版权作品,未经授权严禁转载。转载须注明来源、原标题、著作者名,不得变更核心内容。)




















最新评论: